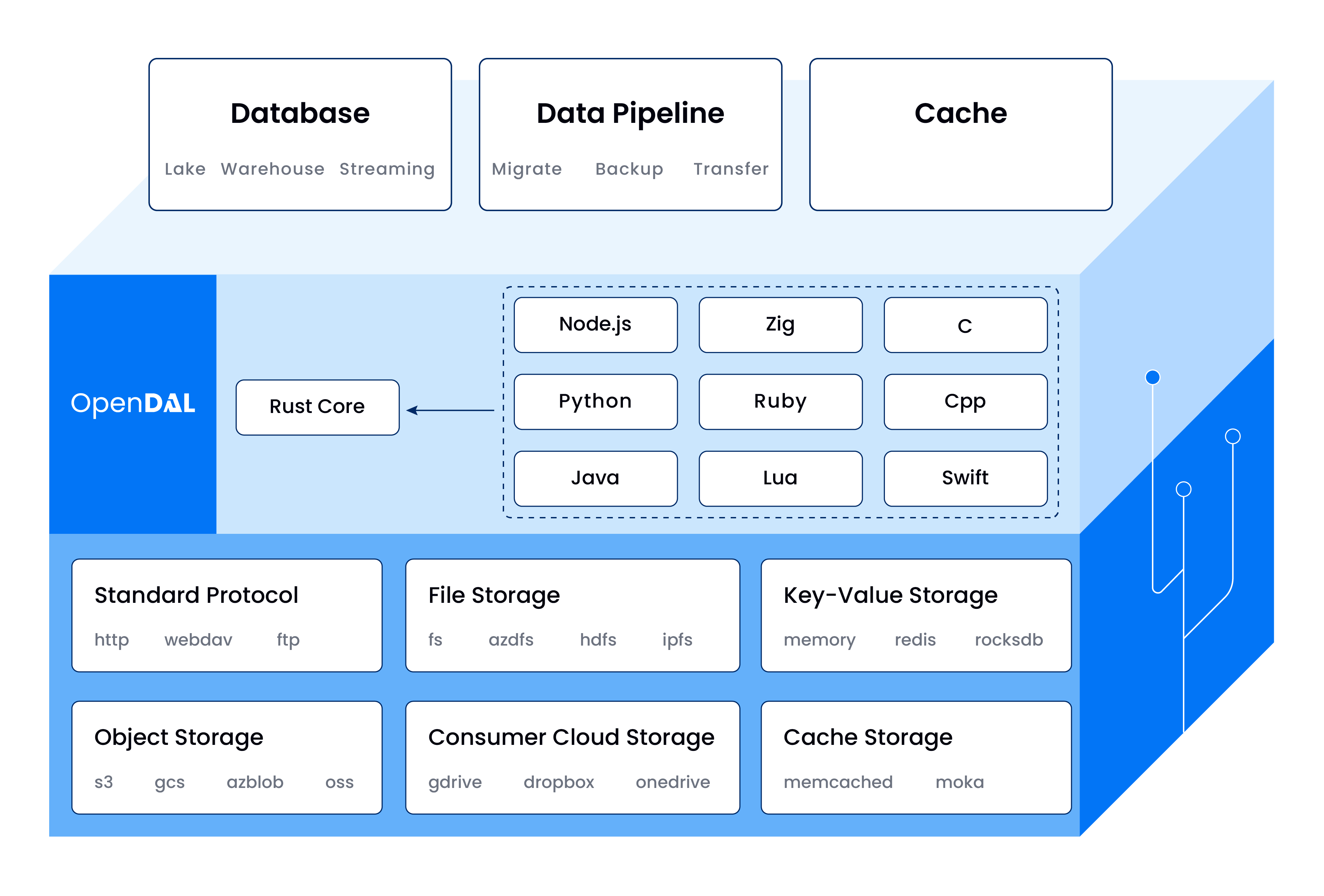中国不缺好的开源开发者
过去数年,我从参与 Perl 6 和 Apache Flink 等项目出发,逐步进入到开源的世界当中。我在 2019 年成为 Apache Flink Committer,2020 年成为 Apache Curator 的 PMC 成员,2021 年全力投入 TiDB 社群的建设,2022 年成为 Apache 软件基金会(ASF)的正式成员和孵化器导师并接连帮助三个开源项目加入孵化器孵化,2023 年成为 Apache ZooKeeper Committer 和 Apache Pulsar PMC 成员。
在这个过程里,我持续接触到了风格各不相同的开源社群和开源开发者,并逐渐认识到中国开发者是开源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:中国不缺好的开源开发者。
然而,当下大部分人讨论和评价中国开源的现状时,往往会认为中国开源距离全球主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。《中国信息化周报》撰文提到,中国开源“整体呈现‘散似满天星’之势,还未形成‘聚似一团火’的强大合力”。
立足现状,我想以一个普通的开源开发者的视角,分享我所遇见的高水平中国开源开发者的形象,进而讨论从开发者个人出发,为建设好中国开源做贡献的几个可能的探索方向。